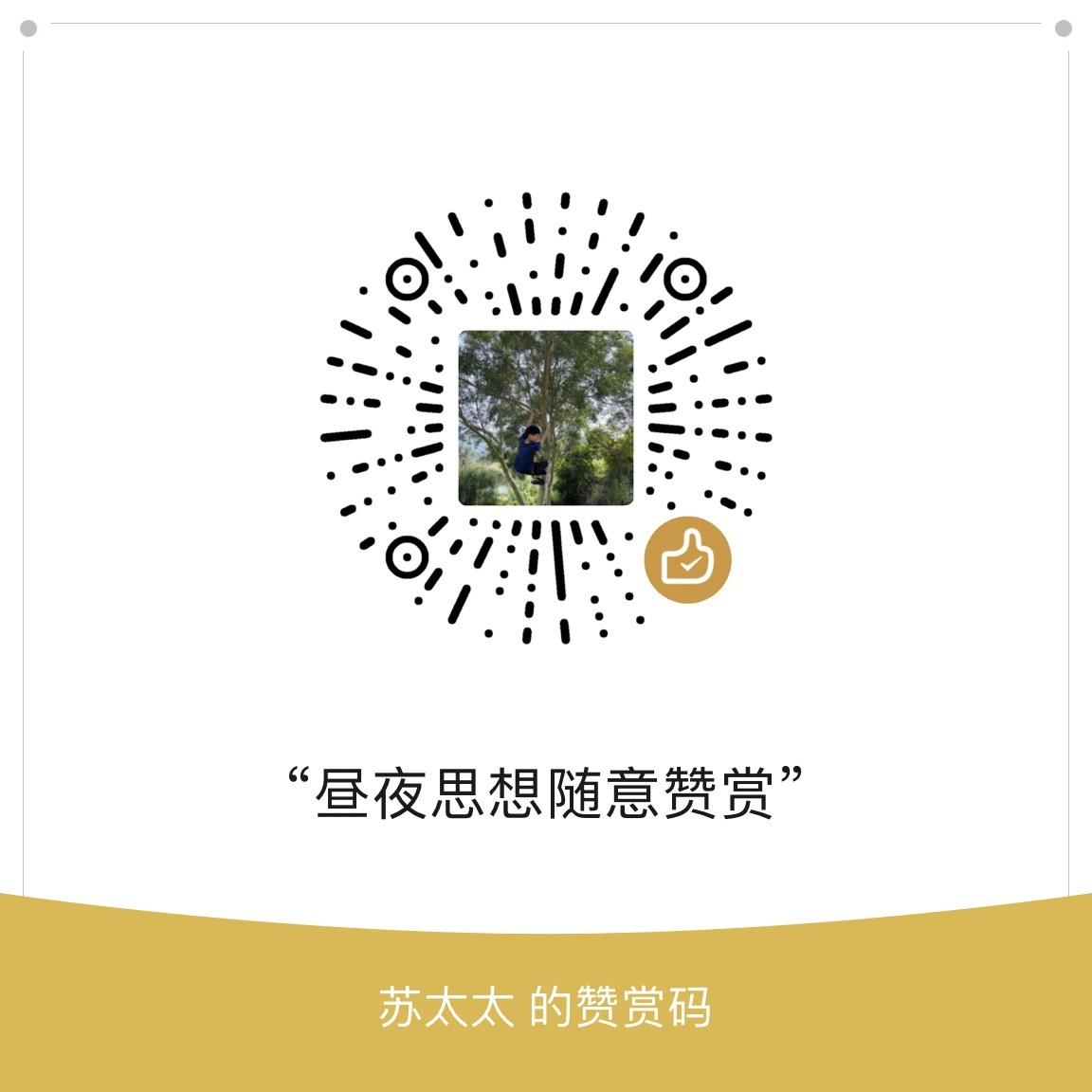小时候看的故事书使我对约拿的印象总是这样:卷曲的黑色胡子、纤细修长的四肢、满脸戾气和耷拉着的眉毛,往往身上还挂着少许的海星并藻类。它们很好地刻画出了约拿的骄傲和悖逆,但却使约拿的形象变得死板,在这个故事中,上帝要拯救的是尼尼微人,而约拿只是上帝的工具。无论他的戏份多么重要,也就是个听或不听从上帝的先知,一切个性的体现不过加深了其悖逆的程度。故事慢慢变得索然无味,大鱼和蓖麻也只引发有限的兴趣,然而,当再读了卢云《浪子回头》之后,我迥然发现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竟与约拿的故事如此相似。约拿受到上帝的启示,是与上帝有紧密关系的先知。约拿选择了逃离,前往远方的他施。约拿让我们看到,对异国他乡之繁华的适寻并没有合理的余地,从一开始就是“躲避耶和华”。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家甘愿放弃未来,而是为了所谓的未来无情无义地抛弃了自己的家。鱼腹中的祷告无疑就是小儿子的回转,奇妙的是,约拿继而走上了大儿子的道路。他为着天父无偿的接纳大大不悦,甚至发怒。
约拿书在约拿与上帝的对峙中戛然而止,正如大儿子矗在家门之外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没有回答,约拿也没有回答。约拿就其发怒的解释与大儿子有所不同,大儿子提出父亲的爱是偏心的,但约拿却说他早就知道耶和华的爱。可是,父亲也爱大儿子,他不是不知道父亲的财产都归他,约拿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慈,他才刚从鱼腹中被解救出来。约拿在理性和经验上都清楚上帝的爱,但为什么他无法共情,而是控制不住地发怒?约拿的逃避不是因为上帝在差他做无用功,因为去他施远比来尼尼微更加麻烦,也就是说,约拿不是不愿意去爱,他渴望活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大儿子约拿认同一个怜悯、慈样的父亲,但当父亲告诉他自己一定会接纳小儿子,要约拿亲自去把小儿子召唤回来,他还是无法心甘情愿地爱。
这对约拿而言是个极大的试炼,他不是在质疑神的爱,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爱是神的本质,当他无法像神一样无偿地、白白地爱时,他选择了逃跑。约拿既是大儿子亦是小儿子,他在两个身份两重关系上都失败了。约拿的故事不只是要我们作出选择,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我们选择不了。约拿故事的未完成和未回答是在等待在指向新约中耶稣的回答和他的行事为人。
在新约里,耶稣以约拿的故事来回应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求神迹,耶稣就告诉他们,这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 外再无其它,而约拿的神迹从两个方面针对我们,提醒也安慰我们。神爱那些罪人,从里到外与他背道而驰的人。并且不仅于此,上帝与约拿的关系、对约拿的救赎更是真正的神迹。而耶稣来了,就使我们这些罪人这些约拿有了回答的可能。
这正是为什么耶稣比约拿更大,耶稣莫名地爱,当客西马尼,爱使他不舒服,汗如雨滴如血点般落下,但他并没有逃避,也没有跑到其它星球上。
约拿逃避身体和心理上的不舒适,他安然沉睡,但上帝找到他并把他剥离,在鱼腹、在城外。于是陷入了昏沉,肉体和灵性。但这仍是个救赎的故事,在鱼腹之中约拿道出了救赎的秘语,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然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心灵发昏的时候,就想起耶和华。”
约拿带来的启示在于,他没有也无法强迫自己理解并效法那超越之爱。如果大儿子因为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装出笑脸欢迎弟弟,故事就不一样了。约拿没有因为自己是上帝的先知就作出符合身份的样子,他发怒不加掩饰地质疑正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
此刻,信心是无能为力时的呻吟。昏沉中的呢喃和哭泣是最美也是这个罪恶时代唯一可能的音乐,愤怒、失控、怨恨正是约拿体会无条件之爱的基础,如果上帝发怒,按照约拿的要求击杀他,他又怎是上帝呢?